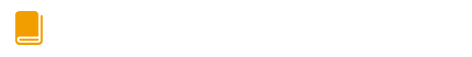
 剧本app下载
剧本app下载
 剧本公众号
剧本公众号

天黑时,土匪盘踞的天鹰山起了大火,火光照亮了天空。山下的庄稼汉们躲在门后,门缝透进来的线状红光印在他们脸上,像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刀疤。天鹰山上顽固无比的土匪,终究被朝廷消灭了。
几天前,来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一路迤逦穿过田野,庄稼汉们没看出与前几年的另外几支剿匪部队有何不同,他们慨叹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不久就要埋骨异乡。直到天鹰山在火光中抖动,他们才回忆起,这支部队打村庄经过时,队列整齐,铠甲鲜明,士兵的眉宇间全是杀气。
这次剿匪,总兵石镇海与知州张少甫谋划了很久。他们不想重蹈之前的覆辙——剿匪不成,反而丢盔卸甲、损兵折将,进而让半生的宦海沉浮成为无用之功。
匪患近来呈愈演愈烈的态势。朝廷中的同僚多次弹劾,尤其是御史大夫田中义,言辞格外激烈,恨不得皇帝直接下诏摘掉他们的乌纱,再治予重罪。石镇海与张少甫分别是在吏部尚书与礼部尚书的来信中获悉的。两位尚书虽然没有明言,他们仍然感觉到了后脖颈凉气*人。
石镇海与张少甫踱来踱去,在总兵府摇曳不止的烛影中,轻便的官靴踩在木板上发出嗒嗒的声响。天鹰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不知牺牲多少士兵的生命才能换得剿匪成功。在石镇海看来,太大的代价会给谏官提供另一种口实。而在张少甫看来,武力征剿并无胜算,总兵大人给他的印象像是善人,而不像是屠夫。两人忽然停住了脚步,互相在对方的眼睛里找到了相同的两个字,于是脱口而出:“招安。”言毕,两人对视而笑。
总兵吩咐摆起了丰盛的酒宴。石镇海连干三杯,张少甫不胜酒力,以浅啜相陪。张少甫突然想起五年前南啸天曾经拒绝过招安,喃喃说道:“南啸天会同意吗?”
石镇海夹起一块*的猪头肉送入口中,嚼了两口,回味了片刻停留在上颚的肉香,说道:“是人就有价码。我许他一个游击,我就不相信他不动心?我的义子房龙你也认识,他随我戍边,立下了许多战功,才不过累迁至游击。”
“不过,总兵大人,招安是某种程度的示弱,”张少甫眉飞色舞地说,“因此,前去招安的人选必须胆略过人,让南啸天感受到朝廷可刚可柔,刚柔并济;可恩可威,恩威并施,从而慑服于朝廷的天威。”
朝露打湿的演兵场,光秃秃地寸草不生,飞扬的尘土中夹杂着汗腥味。总兵帐下的将士全都上身精光,块状的肌肉随着动作此起彼伏,下身肥大的裤子已经湿透了。游击房龙在队列前面挥枪演示,一杆银枪吐出万朵梨花,演兵场上万杆长枪吐出万万朵梨花。张少甫在看台高处赞不绝口,连称“虎父无犬子”,石镇海仅是拈须微笑。
一位少女侧骑骏马来到看台,然后跳下马来。这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云层里穿出,并不耀眼,放射出如血的光芒,照得将士一片通红,在张少甫眼里,刹那间,万千将士像是万千通体赤色的天兵天将。站在队列前面的房龙,持银枪在手,人跃在空中,好似正从九天之上降落到凡间的天神。张少甫目瞪口呆。
跃在空中的房龙使出一招必杀技,并以声助阵,万千人一齐模仿,大呼:“哈!”声如狮吼虎啸,端的是地动山摇。张少甫倒退两步跌坐在地,随后爬起来抱住石镇海的手臂,兴高采烈地说:“武力剿灭!武力剿灭!”石镇海平静地摇了摇头,张少甫怏怏不乐地走到一旁,继续观操。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落在塞外游牧民族的骑兵身上时,石镇海也曾以为那或许就是天兵天将,可是天兵天将们攻不破他的城池,留下了一堆横陈的尸首,和注入大地的人与马的淋漓鲜血。
骑马的少女在通红的晨光中宛若一朵艳丽的桃花,初绽花朵一般的鲜嫩活力,在房龙心田诱发出一种甜蜜与酸涩交织的情感。少女蹦蹦跳跳地跑向石镇海。持银枪跃起的房龙停滞在空中,从这一刻起,他将忘记韩员外的婢女小桃,想当初,他是无意中偷看到韩员外与小桃行苟且之事才愤而投军的。
少女搂住石镇海的脖子,说道:“父亲,妈妈让我问你:今天是否还去霄云寺上香?”
“当然去啰。”石镇海从脖子上解下女儿的手臂,回头看了一眼演兵场。少女顺着父亲的目光,看到了青年将军房龙,他隐藏好了内心真实的想法,再度舞起了银枪。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平生一个念头:这个人可能会教她骑马。
石镇海在去上香之前对张少甫说:“就是他了。”
张少甫不解,道:“就是他了?”
在晦暗的聚义大厅里,坐在虎皮交椅上的南啸天威武挺拔,气度十分不凡。房龙暗暗心惊,张少甫在那次阅兵后主张武力剿灭,外战带给他的骄傲让他在心里是同意的,现在他终于意识到石镇海招安策略的明智。一个大胡子头领一脚踹在房龙的膝弯处,房龙一个趔趄,然后重新站稳身形,腰杆挺得笔直。大胡子喽啰手提一根棍子,欲把房龙打跪为止,南啸天身旁坐着的一位银髯老者,手中捏一本书,他把书在空中晃了晃。大胡子斜瞅了房龙一眼,不服气地退到一旁。
“我倒要看看,”南啸天说,“这次朝廷对招安的重视程度。”
房龙蹙眉道:“在下官拜游击。”
“空口无凭。”
“可惜我没带印信……”
“带了我也不看。”
一阵山风吹在松树上,在山顶的一块平地的四周,传出如同女人衣裙曳地的窸窣声。房龙从兵器架上*出长枪,耍了一个枪花,枪头的红缨像狮子的脖毛愤怒贲张。南啸天束紧腰带,也取了一杆枪,倒握在手中。锣鼓响后,在众多土匪的围观之下,两人枪来枪往,战成一团。
两人的枪法均十分娴熟,起先好勇斗狠,招招不离命门;而后,双方见彼此均难以取胜,枪法转向轻盈灵巧,或攻或守,或守或攻,一招之下变化万千,令人目不暇接。观战的匪兵站得累了,不少盘腿坐在地上,间或为一两招奇妙的枪法大声喝彩。约摸打了两个时辰,两人都是汗流浃背,如沐瓢雨。
南啸天跳出战圈,把枪往地上一扔,说道:“兄弟,我们洗个温泉澡,然后喝酒去!”
房龙道:“相信我是游击了吗?”
南啸天笑道:“兄弟,你便说自己是总兵,我也信了!”
温泉水从石缝中往外流泻,蜿蜒曲折地流至低洼之地,再由低洼之地漫出,在悬崖上挂起一幕瀑布。南啸天泡在温泉水中,一仰脖,喝起大胡子头领递过来的一壶酒。大胡子头领送酒之后没有立刻离开,俯身贴在南啸天耳边,说道:“胡先生说,这人太过了得,不如杀了吧!”南啸天摆了摆手。
在大胡子与南啸天咬耳朵之时,泡在温泉中的房龙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猜到这可能是一句与他生死攸关的话。见南啸天摆了摆手,他才稍微安下心来。南啸天将自己的酒壶凌空掷过去,房龙一把接住,咕嘟嘟地痛饮了好几口。酒劲上冲,他获得了腾云驾雾般的感觉,今天的比武在眼前重现,他想到,如果南啸天征战边陲,现在的地位不会在他之下。
“好酒!”南啸天伸手从房龙那里要回酒壶,连喝了几口,往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道,“兄弟,五年之前,朝廷派来的招安使者,自称是位武将,可是在我手下没过三回合,就被我一枪扎死。接受这样的人招安,对我来说,无疑是种耻辱。”
“石总兵大人可是威震夷狄的当朝名将。”
“我不认识他,兄弟,我认识你,知道你十分厉害。招安的事情,我可能比你们想得开。因为,兄弟,你我都是有本事的人,我们生来就是要吃香的喝辣的。在朝廷混,在山寨混,地方不同而已,我们注定都会是人上人。如今朝廷果真有诚意给我一个合适的地位,并安排好我手下的弟兄,我何必继续落草为寇呢?”
房龙听闻此言,比在聚义大厅见到南啸天那会更为惊心,他没想到南啸天模糊了朝廷与土匪之间的界线,而千万百姓的区别仅在于能与不能,却也言之成理。不过,他没有忘记,刚刚他还想到南啸天如果戍守边关,可以建立与他一般的功业。
“不过,兄弟,我有个条件,游击不游击倒也罢了,”南啸天接着说,“总兵石镇海石大人的女儿石全美必须嫁与我为妻。这样,我就与石总兵的*命运与共,招安之后,我再无后顾之忧。”
“这个……”房龙的脑海里蓦地闪过绽放的桃花的影子,他顿了一顿,说,“我得请示总兵大人。”
尽管房龙与张少甫、总兵夫人旗帜鲜明地站在石镇海的对立面,然而,这位总兵大人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他坚持要以自己的女儿换取和平。在他的戎马生涯中,对待战事,从未有过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心绪低沉,精神疲倦。作为一名从中年步入暮年的幸存老兵,他只想抓住生命里的最后一点光阴,平静淡泊而又有滋有味然地度过余生。
想起从前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扭曲面孔,他既没有了紧张激动,也没有了麻木不仁,有的仅仅是愧疚不安,石镇海明白自己不可能再在疆场厮杀争胜了。他把义子房龙留在身边,他对他的情绪却是奇怪的:一方面厌烦他与他一样双手沾满鲜血,一方面却不得不在同样令他厌烦的军事事务中依赖于他。张少甫、夫人和房龙的意见,在他都不是问题,他留心到女儿沉默不语,粉红的脸上浮现羞涩的红晕。
“只要女儿同意,”石镇海说,“我想带她去见南啸天一面。”
自从那天清晨见到威武的军容,张少甫满腹的心思全是武力剿匪,招安与武力剿灭的功勋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他没有料到石镇海如此固执己见,在“和亲”的是石镇海的女儿而不是他的女儿的情况下,他不便太过争强。他只能寄望于石全美不同意。
可是,石全美以手掩面,轻轻地点了点头。张少甫看到总兵夫人羞愧难当,几乎拿起茶杯将一壶茶泼在石全美脸上,她在半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压下了无名之火,胸脯却激烈地上下起伏。
这样的结果,房*本没有想到,当他教石全美骑马时,疑问依旧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石全美一忽儿上马,一忽儿下马,快乐得像一只鸟儿,房龙的疑问无从出口,他怕破坏这份快乐。草丛中突然飞起一只野雉使马儿受到惊吓,它直立起来,石全美尖叫一声从马背上摔下。房龙来不及接住她,他扑在地上,石全美落在她的身上。
房龙抱着吓得晕过去的石全美,她柔软的身体像是一张波斯毛毯,在白云飘浮的瓦蓝天空下,他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沉醉在幸福之中。
石全美悠悠地醒转过来,小心翼翼地保持原封不动的姿势,她感觉自己像一只暖和的小猫。她看了看他正在看的天空,天空上漂浮着几朵白云,她看了看受惊吓的马儿,它在咀嚼青草。她想,一个人如果可以同时去爱两个人该多好啊。
在天鹰山下见面的那一天,两只云雀从双方的队列间飞过。双方各带了三百来人。南啸天弯弓搭箭的同时,房龙也弯弓搭箭,空中穿过两道白光,随后两支串着云雀的弓箭在同一时间坠地。两队人马一齐击鼓,连躲在门缝后观瞧的庄稼汉们都禁不住低声喝彩。
石全美在两人神勇的表现面前再度迷惘,她陷入深思,无力作出取舍。两个人都是这般仪表不凡,武功超群,又擅出风头。最后,她想到,她有机会成为一名土匪头子的压寨夫人,禁不住快乐得浑身发抖。面对父亲的询问,她避开房龙充满爱意的目光,紧咬嘴唇,用手指了指南啸天。南啸天在对面看到她的手势后哈哈大笑,笑声传来,石全美两颊绯红。南啸天*出一支箭,再次搭弓,故意朝石全美瞄了瞄,然后放回箭壶。
在南啸天向石全美假装射箭的当儿,一支忠于房龙的部队在张少甫的鼓动下,以保卫石全美的安全为口号,向土匪发起攻击。石镇海没能制止部队的行动,他的命令在震天的鼓声中微若蚊吟。他一怒之下,带领女儿拨马就回。
土匪对此早有准备,两支土匪分别由大胡子和军师胡里率领,从天鹰山侧翼冲出,三面包夹官兵的部队。张少甫虽然骑了一匹雄壮的马匹,但由于它不谙战事,在鼓声中屁滚尿流,卧在地上筛糠不止。张少甫犹*马背上一动不动。房龙一把提起张少甫,放在自己的胸前,挥舞长枪,且战且退。
第二天,在天鹰山土匪长胡子的指挥下,山下的庄稼汉们挖了一个深坑,掩埋尸体。他们悄悄地数了数,官兵阵亡124人,土匪死了39人。他们生前杀个你死我活,死后却长眠在了一起。
霄云寺建在霄云山上,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由于战火连绵,霄云寺多次遭农民起义军焚毁,现存的霄云寺是五十年前重建的。在总兵一家去霄云寺上香的那次,南啸天与石全美初次相见。
石镇海并不信佛,然而其夫人是位虔诚的居士,在二十年的随夫漂泊生涯中,她从未忘记礼佛。这位总兵夫人是当朝吏部尚书的侄女,年轻时脾气急躁,性格火辣,对人丝毫不留情面,经过多年的佛学浸染,渐渐能够克制火气。
总兵一家微服到霄云寺上香,引起霄云寺上下的极大震动,主持戒嗔和尚得到这一消息时,脸色与平时毫无区别,心中却长念了数声“阿弥陀佛”,在步出禅房时脚磕在门槛上,差点跌倒。他吩咐僧众将佛堂闲杂人等一概清理出去。在这一干人等中,就有南啸天、军师胡里和大胡子。之前不久,南啸天上香完毕,为卜今后吉凶,特意求签,签曰:
一将功成万骨枯,人面桃花相映红。
南啸天不解,问僧众,僧众亦不解。问胡里,胡里道:“第一句是说,你的功业是万千人用命换来的;第二句大概是说,你最近要交桃花运。唐人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按此,似乎这桃花之运并不顺利。但也不甚明了”南啸天道:“原来却是糊涂签。”胡里道:“签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签自然是糊涂签。”
这时,僧众过来清理佛堂,将一干人等驱至门外,石镇海夫妇及女儿石全美走上前来。人丛中的南啸天立刻被石全美吸引,他马上想到了刚才的求签,他默念道:“人面桃花相映红。”少女石全美明眸含情,皓齿带笑,*的脸蛋无有丁点瑕疵,真个是艳若桃花。时值四月,霄云山上佛堂门外,桃花盛开,南啸天吟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行到佛堂门前的石全美听闻有人念诗,回眸一看,望见南啸天冲她挥手,并微微一笑。石全美以眨眼回应,还待看清南啸天面目,却被总兵夫人拽进佛堂。
由主持戒嗔相陪,总兵一家正在叩拜菩萨,忽然听闻门外喧哗,一僧人进来禀告,却是柴房起火了。众人走出佛堂,前去柴房救火,南啸天在混乱中突然现身,一把拉住石全美。石全美不曾害怕,却感意外,刚要张口说话,被南啸天一把捂住嘴唇。南啸天把脸凑近石全美,石全美以为他要亲吻她,脸蛋瞬时通红,譬如早霞,更增十分艳致。南啸天在她耳边说:“我要娶你。”意向中的亲吻没有来临,石全美睁开闭上的眼睛,睫毛闪动,那意思放佛在问:“你是谁?”南啸天道:“我是天鹰山的土匪头子南啸天。”说完,他松了手,走进人丛。
石全美的心狂跳不止。石全美心想:傻瓜,我知道你是谁了,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她拢起双手放在嘴边,对着南啸天威武的背影悄声喊道:“我叫石全美!”
柴房里的火势没有蔓延,很快被众人扑灭,戒嗔声色俱厉地在僧众中查找责任人,并下令今晚停斋一顿,直到找到防火者为止。那天晚上,霄云寺的僧人除了戒嗔和尚外,全都饿了肚子。
其实,那把火是南啸天让大胡子放的。
军政联席会议从上午开到了下午。对于少数官兵在天鹰山下的不服从命令行为,总兵石镇海非常生气,海涛般的愤怒尽情宣泄了出来。他在座位上十多次拍案而起,这比他军旅生涯中的拍案*的总和都要多。可是,他内心深处不免悲凉地想到,他的怒火如此绵弱无力,因为他找不到怒火的来源,军士阵前的不听指挥实际上他根本不当回事,他的进取心在金戈铁马中已经丧失殆尽。
他的怒火做样子的成分要多一些,他明白,如果再不展现自己的权威,他很可能会成为名不副实的总兵。可是,他的部下(不少都是跟随他在边关征战多年)没有人站起来慷慨陈词,没有人站起来宣誓效忠,他们脸上一概是同情的表情。又一次拍案而起的石镇海拿眼角的余光扫视义子房龙,房龙的表情除了同情,更有沉痛和下定决心后的勇毅。哀伤的表情慢慢地浮现在石镇海的脸上。
接下来的几天,石镇海在酒精的半麻醉状态下多次盘点自己的人生,贴身军士向他报告房龙与张少甫过从甚密,他置之不理。不久,他收到了天鹰山匪徒的问责信,这封信里,南啸天强调了官兵前次发起攻击的不义性,并由此对朝廷的招安诚意表示怀疑。不过,他又说,他本人对总兵大人是敬仰的,对他推动和平的努力深表敬意。他把信读完后信手扔在了几案上。
朝廷派来一位钦差,宣布新的人事任命,这是张少甫活动的结果,他许诺把自己年方二八的俏女儿嫁与礼部尚书为妾。皇帝在诏书中宣布,石镇海多年为国征战劳苦功高,现调回京师另有任命,总兵一职由房龙接任。诏书中还说,任命知州张少甫为监军,月内征讨天鹰山,务使一匪都不放过。
在送行的途中,房龙克服了愧意,不亢不卑地与义父和义母说话。前总兵夫人意识到回京师可能遭受到的冷遇,违背心愿地向义子示好,并暗示石全美尚待字闺中。房龙看了看石全美所乘的轿子,她挑起珠帘,给了他一个瞪视的面容。房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平匪成功上。
天鹰山下的庄稼汉们看到一支大约几千人的官军进*天鹰山时,关上门躲在门后观瞧,他们想到,第二天又得带上铁锹,在大胡子的指挥下埋葬官军与土匪的尸体。然而这次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大胡子第二天没有派人来叫他们。战斗打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夜里,听不见厮杀之声,却看见天鹰山起了大火,火光照亮了整个黑暗的夜空,照亮了山下庄稼汉们居住的村庄。
红色的火光透过门缝印在庄稼汉们的脸上,像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刀疤。他们不无惋惜地明白,这一支在天鹰山附近纵横多年的悍匪,终究被朝廷消灭了。他们在天鹰山抖动的火光里回忆起,这支官军与前几年的另外几支征剿部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打村庄前面经过时,队列整齐,铠甲鲜明,士兵的眉宇间全是蒸腾的杀气。
翌日清晨,得胜的官军衣衫破烂,从天鹰山上脚步踉跄地走下来,他们的人数不及来时的五分之一。士兵们抬着一杆沉重的银枪,那是新任总兵房龙的,但他没在队伍里。没有出现把天鹰山上的土匪多年聚敛的财富肩挑背扛运下山来的场景,想是那一场大火烧尽了山上的一切。山下的庄稼汉们远远地站在土坷垃上,看到衣衫凌乱、灰头土脸的官军,几个胆大的庄稼汉忍不住笑出声来。官军的回军路线并不经过村庄,他们看到庄稼汉们之后,掉头朝这边开过来。
庄稼汉们纷纷逃回各自家里,闩上门,又搬来桌子、棍子,死命地抵住门。官军分散开来,包围了所有人家,不给开门的,一律点火烧房。房顶用来遮风避雨的茅草,很快被火烧成灰烬,露出烧黑的土墙。中午,官军汇聚在村中的空地,由庄稼汉们杀牛、猪、犬、鸡,由庄里的婆娘烧煮,开了十多坛子酒,官军的大会餐正式开始。吃完后,醉醺醺的官军没有离开,他们钻进庄稼汉们的屋里睡觉、骂人、砸东西。
第二天清晨,下起了大雨,这场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官军就是在雨中离开村庄的,大雨浇得他们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离开时,官军没有任何队形,像逃荒的难民,每个人手里拿着一点点财物。村民之后的哭声追上这支得胜回师的官军耳中,他们加快了前行的脚步,一些士兵扔掉了手里的财物,后面的士兵把扔掉的财物又捡了起来。
经过官军骚扰的村庄,好像是鏖兵后的战场,房屋在雨中摇摇晃晃。几个想不开的女子,吊死在房梁上。
与朝廷军队的多次对抗中,天鹰山的土匪从未遇到过房龙这样的劲敌,通往天鹰山聚义厅的道路是官兵用尸体铺成的。房龙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浑身轻伤二十余处,战袍沾满了鲜血。他下了命令,如果他战死,生者必须继承其遗志,直到消灭山上土匪为止。
在三天三夜里,官兵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天鹰山的土匪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消耗战中伤亡惨重。南啸天杀红了眼,一人杀死了二十余名士兵,曾有两箭射中房龙,不过都非要害。
官兵抵达山顶后,在失去地利优势的土匪面前推进很快,用了一炷香的工夫就完全占领了聚义厅。军师胡里命令匪众四处纵火,山上的建筑(包括聚义厅)、松木片刻就笼罩在火海之中。火光成了战场最好的照明。蜂拥的官兵将土匪赶到瀑布处,其下,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一通砍杀,聚在悬崖边的土匪仅剩下三十余人。现在,房龙与南啸天的距离不足十米。
军师胡里取出粗绳缚在一块巨石上,另一端扔下悬崖,恳请南啸天缘绳逃生。南啸天扔下长枪,眼含热泪与胡里、大胡子相拥作别。房龙看到南啸天逃走,率领士卒大砍大杀,急欲冲过去砍断绳索,奈何土匪众志成城,拼死抵抗。
胡里、大胡子最后被杀死的两名土匪,他们都死在巨石边上。有士兵准备斩断绳索,房龙连忙喝止,他往回拉拽绳索,另一端并无重物,看来南啸天逃出了生天。房龙把银枪交予士兵,在一片“不可”声中,顺绳而下。瀑布的水流击打在房龙的身上,在呼吸中连呛了几口,禁不住大声咳嗽起来。他感到绳索经水的绳索异常湿滑,急忙手脚并用,牢牢攀住绳索。
从悬崖往下约有一百米,是一水潭,周围树木葱郁,夜色下迷蒙不清。房龙游过水潭,在地上歇坐了片刻,然后昏暗中不辨方向地朝前走了几百步,眼前豁然开朗,天鹰山上的火光照到了这里。这是一块方圆几百米的平地,上面只生杂草,未长树木。房龙看见,火光中跳动不止的南啸天,湿漉漉地坐在草地中央,手按佩剑,正拿眼瞅他。
意外相见之下,房龙倒退两步,几乎掉头逃回。他马上想到,悬崖之下,已无可逃之地。对去往京师途中的石全美的想念,给他增添了几许狠劲。他想到,只有击毙匪首南啸天,这次剿匪方竞全功。他为刚刚的倒退两步感到羞惭,*出腰中宝剑,挺身走向南啸天。
南啸天坐在地上,仰望天鹰山,山上大火没有熄灭,股股浓烟窜向高不可测的天空。现在他孑然一身,亡命天涯却不可得。两千人的天鹰山,数十载的经营,就毁在这三天三夜的战斗中,就毁在这一把大火之中。“一将功成万骨枯”,霄云寺的签大概预示的就是这样的结局吧?那么,他与房龙之间,谁会是剩下来的那“一将”呢?他站起身来,他的杀气浸透了佩剑,佩剑发出铮铮的鸣响。
两人在三天的战斗中几乎都没有合眼,在生死面前,他们鼓起余勇,没有精巧的招数,只有笨拙的砍杀。在砍杀中,房龙与南啸天各自挂彩,突如其来的疼痛让伤者清醒,马上对砍杀者施以新的剑伤作为回报。他们连杀了几个时辰,最后连剑都已经拿不住,在第二天的第一缕晨光中,他们全都倒地不醒。
他们在和煦的阳光中睡了一天。傍晚时分,房龙被一种浑厚的吼声唤醒,他睁开疲惫不堪的眼睛,感觉到刺骨的寒意,模糊不清地看到南啸天躺在身边,他坐起身,捡起宝剑刺向南啸天的咽喉。这时,那种浑厚的吼声再次响起,房龙看到一只雄壮威猛的动物从林子中走来。他那一剑没有刺下去,用脚踢了踢南啸天,喊道:“老虎!”南啸天翻了一个身接着睡去。房龙用剑扎在南啸天的腿上,南啸天吃痛,翻身坐起。
他们睡眠后恢复的一点力气,帮助他们杀死了老虎,他们的身上,再添几处新伤。用钻木取火的方式,他们生起了一堆火,烤起了虎肉。他们早已饥肠辘辘,没能尝出虎肉是什么滋味就已经下肚。共同参与的生死战斗,让两个对头间获得了部分的信任,相约第二天白天再清理他们之间的生死账目。
那一晚,他们睡得都很不好,他们坐靠参天大树的树干,各自把剑抱在怀里,在平地的两端彼此监视,以防对方不守约定偷摸下黑手。在早晨的大雨来临前,他们感到空气有点闷热,却特别适合酣睡,于是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大雨就是在这一时刻来临的,*的雨点落在树梢的叶子上,很像是一群女子细碎的脚步。惊天的霹雳声中,他们惶惑不安地醒来。南啸天看见低沉的乌云向他们的方向排山倒海地移来,扔下佩剑,脱下衣服挂在树杈上,跑进了雨中,来到烧烤老虎的平地中央。房龙惋惜这样一位值得尊重的土匪头子竟以癫狂收场。
大雨落在白光光的南啸天身上,汇成细小的水流流下,他仰着头,平举双手,好像是叩问苍天。他忽然转过头来,对房龙说:“扔掉宝剑,到雨里来!”房龙对他荒诞不经的话语没有作答。两块低沉的乌云撞击在一起,制造出一道闪电,好像阴暗的雨天同时升起了十个太阳。随后,震击耳膜的霹雳响起。房龙不远处的一棵大树被拦腰斩断,斩断出冒出烟火,不久,被大雨浇灭了。
房龙犹豫不决。南啸天看了看天,两片不同方向的乌云聚过来,他说道:“快到雨里来!”房龙迅即脱去衣服,也仿照南啸天那样挂在树杈上,提着宝剑往雨里走来。南啸天连忙道:“扔掉宝剑!”房龙会心地一笑,表明此时此刻,他绝不会加害于南啸天。南啸天冷冷地道:“闪电专爱打宝剑。”
南啸天话犹未了,两块乌云又撞击在了一起,这次是更耀眼的闪电。闪电恰好打在房龙刚才倚靠的大树周围的那一片,几株高大的树木同时倒下,巨大的树冠的落地声响,被震耳欲聋的雷声淹没了。
暴雨过去,下起了大雨,南啸天与房龙回到各自的树下。南啸天抹掉身上的雨水,穿好了衣服,房龙从覆盖的树枝中找到了衣服,也穿在了身上。
大雨下了三天三夜。
天放晴之后,他们再度举起剑来。他们注意到,对方的眼里布满了血丝,颧骨变得突出,身形变得消瘦。此外,还有整个身体体现出来的*无力,只需要一个普通的士兵,就可以杀死他们。这都是在短短的几天内发生的。
但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他们举剑格杀,每一剑都是缓慢而潦草的,他们提心吊胆地想到,手中的剑可能被对方击落。房龙以剿匪、升官、得到石全美来鼓励自己;南啸天以为弟兄们报仇、为逃出生天来激起勇气。他们打打停停,在山里绕来绕去。渐渐地,每一次战斗的时间,赶不上每一次休息的时间长久。
他们用了两天时间,从山里转了出来,最后,无意中爬进了天鹰山下的村庄。此时,他们的衣衫一条一条地挂在身上,上面沾满的血迹又被地上的泥泞掩盖了。他们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爬进一户燃起炊烟的人家,宝剑与佩剑都掉落在门外的地上,然后趴在干燥的地上气息微弱地喘气。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妪手里拿着锅铲,站在厨房门口,惊奇地看着他们。
老妪认不出他们一个是威武挺拔的天鹰山匪首南啸天,一个是武功超群的新任总兵房龙。他们都是一脸泥土。他们的部下此时也不会认出他们。老妪不管他们,让他们趴在堂屋的地上,自己一边煮饭,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话。
老妪说,丧尽天良的官兵啊,连土匪还不如,*了我的孙女,我相依为命的孙女上吊了,才十七岁啊。老妪擦了一把眼泪,接着说,当百姓最可怜,当朝廷不成,当土匪也好啊,可以收税,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说什么别当百姓……他们都上了天鹰山当土匪去了……他们不要我,他们嫌我老,其实我还可以烧饭啊……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吗?听见了就回答一声,我煮稀饭带你们吃……
老妪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搬到后院的坑里,这个坑,也是花了她很大的力气才挖成的。临死前,房龙想起了桃花,漫天的桃花缤纷地柔软地落在他的肩头;南啸天则想起了那支签,他不明白“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一将”会是谁,但肯定不是他和房龙,接着,他想到了那支签的下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红”,他觉得整个人都融化在三月桃花绽放的暖意中。
青草在坟头很快扎起了根,一阵清风吹过,它们在坟头轻轻地摇晃。几滴眼泪落在它们身上,它们以为是期盼的雨,简直要唱起歌来,一双芊芊玉手却把它们从坟头连根拔起,远远地扔到了一边。石全美在坟头静立了半晌,她想起在霄云寺时的南啸天,想起被她压在身下的房龙……两个可爱的男子汉都去向了另一个世界。
老妪在一旁与总兵夫人喋喋不休地说话,没有注意到总兵夫人一起紧皱的眉头。再度回来任总兵一职的石镇海看到石全美没完没了地流泪,让夫人把她从坟头拽走了。石全美仍在不时地回头,一抔黄土之下,曾是两个伟岸的生命。
石镇海是在剿匪结束之后三个月官复原职的,他们仍被朝廷派来出任总兵。上任之后,他派人四处打听房龙和南啸天的下落,有一天找到老妪家里,凭借两把剑,以及老妪的口述,确认埋在后院的两个人就是房龙和南啸天。
对于天鹰山新聚起来的土匪,石镇海依旧准备推行招安政策。天鹰山的新匪首提出,首要条件是,必须让他娶石全美,这样他才能确保招安后没有后顾之忧。张少甫和总兵夫人都不赞同招安,主张武力征剿,但石镇海决定,由石全美本人决定是否同意土匪的条件。一听说要嫁给天鹰山的匪首从而当压寨夫人,石全美禁不住快乐得全身发抖。
专业定制代写小品、相声、话剧、舞台剧、戏曲、音乐剧、情景剧、快板、三句半、哑剧、双簧、诗朗诵、演讲稿、微电影、动画等各类剧本。联系电话:13979226936 QQ:652117037 公众号:剧本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