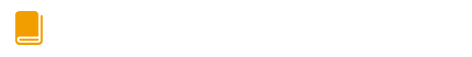
 剧本app下载
剧本app下载
 剧本公众号
剧本公众号
 喜剧电影剧本
喜剧电影剧本
 偶像电影剧本
偶像电影剧本
 农村电影剧本
农村电影剧本
 都市电影剧本
都市电影剧本
 儿童电影剧本
儿童电影剧本
 历史电影剧本
历史电影剧本
 军旅电影剧本
军旅电影剧本
 古装电影剧本
古装电影剧本
 武侠电影剧本
武侠电影剧本
 警匪电影剧本
警匪电影剧本
 恐怖电影剧本
恐怖电影剧本
 动作电影剧本
动作电影剧本
 科幻电影剧本
科幻电影剧本
 神话电影剧本
神话电影剧本
 悬疑电影剧本
悬疑电影剧本
 穿越电影剧本
穿越电影剧本
 其他电影剧本
其他电影剧本
 剧本杀剧本
剧本杀剧本

人物:陶今恃(今子,金子) 林文秋
孟学平(陶今恃的丈夫) 周晓洁(林文秋妻)
根他妈(卖茶大妈) 大妹(根他妈的女儿)
徐卫民(中学老师) 陶唯一夫妇(今子父母)
翠敏(今子表外侄女) 孟学平的父亲(市委常委),母亲
一、
音乐:车站。
字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一条弯弯曲曲的简陋公路,一棵巨大的樟树。
樟树下现出一个风雨亭,这个风雨亭,四根柱子顶着一个平脊屋顶,屋顶是用黑瓦盖的。这风雨亭在四野的景色中,象绿叶溶入了树林一样。它三面砌了墙,根他妈在里面摆了个茶摊。根他妈在忙着卖茶,一幅简朴的乡村风景。
推出字幕:“假日车站。”
风雨亭旁是一歪斜的电线杆,上挂一站牌,上书:樟树岭车站。
陶今恃站在车站旁等车。陶今恃是那种好象从云里走下来的那一种人,虚虚渺渺的,白衬衫掖在裙子里,着布鞋和短袜,是六十年代城里的那种时髦女孩。现在,她站在这里等车。她的身后,是通向这一带村庄的村路。村路弯弯曲曲,伸向那遥远的山里,路两旁是馒头一样平滑起伏的山坡,山坡上种了一垅垅的茶垅,因此人们就看不到路,路被弧形遮住了,人们只看见缓坡的远方在一片淡淡的岚气里,好象隐藏了一个特别神秘的世界似的,给人一种空旷高远的虚虚渺渺的感觉。
车站时有人来。
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乡村小男孩在打量着她,这男孩叫林文秋。
景色在变换,陶今恃一次次地从那小路上走来,形象总不大改变。
画外音:陶今恃每年暑假和寒假都会在这车站出现。
重复陶今恃一次次地从那小路上走来的画面。
每次,只看见她从那小路上出现,开始是头,那么洁净的小巧的头,然后是上身,然后是裙子,慢慢地,飘啊飘的,象是一个不真实的幻影。她就这样飘啊飘的,象一个精灵似的飘过来,又从这男孩林文秋的生活中飘过去,然后消失。
男孩林文秋不相信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就象这山野,从来就有不真实感。
根他妈看守着茶摊,车站是村路和公路交汇的地方,有人坐歇。
这样一个少女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好象没发现过,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小姑娘,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的就长大了?
“这是谁家的囡啊?长得这么水灵?”一个乡里人问。
“啊,啊……这都不晓得!”根他妈一语惊人。
人们一起竖起耳朵听。
“她呀……”根他妈刚开口,又不说了,“你们猜猜?”她打起了哑谜。
山里人朴实,于是,“林家的?”“吴家的?”“邵家的?”一通乱猜。
“猜不出来吧?那陶家坞地主陶老婆子的!——金子!”根他妈毕竟不是城里人。
“是那城里的老师陶唯义的吗?”
“陶唯一!”
“呵,陶唯一啊,会写脚本的,在城里当大学老师,人家本事大着呢。”
“不是不大来吗?现在怎么……?”
“这几年那地主老婆子老了,身体不好了,所以每年假期,金子就会回来,据说还是她自己要来的。”
“喝,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不知是赞赏还是抵牾。
男孩林文秋站在一旁听,不由得露出了蔑视的笑容,既而又有些迷茫。
长夏过去,今天,林文秋知道金子会走,就故意来到这车站,想再看她一次。
今子依然是那样地从那山路上走来,洁净又文静,先是她那小巧的头,然后是上身,然后是裙子,飘啊飘的,象是一个不真实的幻影,从那飘飘渺渺的山间飘来。
林文秋这次是带着一种怜悯的心态来看她的。今子来到小站,依然那么高傲,一声不响。但这次,她看了这小男孩一眼,是那种随便瞟一眼地看了林文秋一眼。好象是在极力回避。她文静地站在一隅,低头看她的书。
汽车来了,她又消失在那尘土飞扬的公路上。
林文秋意绪怏怏地走进茶摊喝茶,根他妈问他:“毕业了?考学了没?”
林文秋回答:“没,进工厂了,在省城。”
根他妈就说:“今子考了高中。”
“哦,是吗,她那种人……。哦,当然,她当然要上大学。”
二、
1966年暴发了文化大革命,到处是红卫兵,大辩论,大字报。
省文化艺术学院内,陶唯一被揪出批斗,他挂着“省三家村黑干将,大地主的孝子贤孙陶唯一”的牌子。大字报写着:“谁为彭德怀翻案,就砸烂他的狗头!”“打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急先锋陶唯一!”“批臭大毒草‘海瑞……!’”
陶唯一挂着牌子回到家里,他怔了怔,突然拿起了菜刀。院子里的孩子们正爬在窗上看黑帮,只见陶唯一拿着菜刀朝自己的脑门就是一刀,孩子们惊叫起来……。
造反派赶来“救他”,踢门,他又一连几刀。
今子的母亲和今子捧着陶唯一的骨灰盒回到樟树岭车站,人们鄙视地看着她们。
紧接着陶唯一的妈也死了,自然是“自然死亡”,陶家坞也就没有了陶唯一这一家人。
六七年春,省博物馆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展。林文秋沿着那些文字、图片、实物一样样看去,在看到一堆砸碎了的寺院佛像时,看见了今子,她是这次展览的解说员。今子穿着庄重整洁的统一服装,人很消瘦。林文秋看见了她,怔了一下,他没想到,象她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解说员?今子看见了林文秋,相互明了的看了一眼,只当不认识。
今子有点急匆匆地讲完了解说,转进休息室,象是逃走一样。从她的背影里,林文秋看得出,她是在极力地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悲痛和惶乱,林文秋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那惶乱的身影一晃,象天边的哀鸿,刻在这惨淡的展览馆和林文秋心中的天幕上。
文艺学院陶今恃的家。
今子母亲对今子说:“上山下乡了,你还是回陶家坞吧,那里是你的故里,再说那里离省城也不远。”
今子点了点头。
于是樟树岭车站又有了她——陶今恃的身影。
陶今恃穿了一身村妇常穿的衣裳,显得瘦弱,也总是那么洁净,不大和人说话,一个人独来独往。
一次次的星期六傍晚,林文秋下车回家,今子上车。
林文秋可以说和她已熟悉了,只是从未说过一句话。现在,今子看到他,会对他笑笑。人的善意能被别人感知到,林文秋的善意今子自然感知到了。她以这种方式对他表示了感激。只要人少,林文秋也回之以一笑,有时,问一句:“回省城?”今子只回答一个“嗯!”字。
一天,林文秋看见今子一人在那空无一人的茶山上。这一天,今子母亲来了,来看望死去的丈夫和婆婆,所以她不去省城。林文秋因在车站没见着她,心绪怏怏。当林文秋来到那平滑起伏的茶山上时,看到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幕。只见今子,今子她在那山头上扬着手地在飞跑,她跑得那么狂野,大声地喧泄着什么,发了疯一样的大笑。
一种凄楚突然攫住了林文秋的心,泪水就涌了出来。
今子跑了过来,看见了林文秋,一下子站住了,接着一转身,捂着嘴地跑了。
林文秋已泪流满面。
林文秋是一个在姑娘面前窘得不行的人。一天,林文秋刚下车,在那次看见今子失态之后。今子看见了他,走了上来,抬起她那明朗的脸,对林文秋灿烂一笑,这是没有过的表示,是她主动在向林文秋示意,表示问候。林文秋涨得一脸通红,有点紧张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下林文秋更惶乱了。在这样的情境中,他就相当粗鲁地没有理今子,走开来。
今子一下子站住,窘得不行,张惶四顾。
汽车里,今子看着林文秋,黯然地闭上了眼睛。
根他妈对林文秋说:“金子病了,她妈接她到省城去了。”
根他妈只对林文秋一人说。
林文秋笑了笑,羞愧地低下了头。
三、
一个朴素的婚礼,今子和孟学平结婚了。
樟树岭车站。
一村妇说:“金子嫁了一个高干子弟,是大学生,待她很好呢。”
另几个村妇说:“这孩子有福气。”
林文秋听到这话,感到不是滋味,但又释然。
根他妈就看着他,摇了摇头。
徐卫民对林文秋说:“今天,我们到省文艺学院去,看一个教古典文学的右派的儿子?”
“省文艺学院?”林文秋问。他想到今子曾住在过文艺学院,就想去见见这个她曾经住过的地方。
“是省文艺学院!”
他们来到文艺学院,向左上了一个高高的台阶,走进一条长长的遮廊。在遮廊那一头,看样子也是一个台阶,今子和一个年青人走了上来。开始是她那洁净小巧的头,然后是上身,就象在那山野时一样。今子没注意到林文秋,在和年青人说话。林文秋不再是当年的农村学生了。一见是今子,立即叫了起来:“今子!”
今子正在说话,没想到在这里会有人叫她,抬起了头。一看是文秋,立即高兴地跑了过来,站在他面前,有点窘迫地看着他,问:“文秋,怎么是你?”
今子身后的年青人,是一英俊的年青人,国字脸,浓的眉,眼睛明晰。
徐卫民看见了他,立即热情地叫了起来,说:“这不是孟老师吗?”
青年愣了愣,才看清,也说:“哦,是卫民啊。”两人握了握手,走向一边。
“你们认识?”今子问那青年。
“嗯。”那青年“嗯”了一声,又说,“这是徐卫民啊,徐老师。”
“这……?你过得还好吧?”林文秋急切地问今子。
“你怎么在这里?”今子没回答他,问了这一句,接着好象是想到了,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丈夫,孟学平。——学平,你过来,这是我家乡的朋友,林文秋……”她叫林文秋是她的“朋友”,真令林文秋感慨。孟学平走上前来,热情地握了握林文秋的手,这是一个有分寸感的年青人。握过手,对林文秋说:“好久没见过面吧?不要紧的,我们没事,来看她妈妈。”
林文秋和今子没多少话好说,怕当着徐卫民和孟学平的面冷了场,忙说:“不了,今天有事,改天吧,今天要去看望一个朋友。”今子当然明白,也不挽留。
“那这样吧,”孟学平说,“什么时候来我们家,有钢笔吗?”他问林文秋。徐卫民说:“我有。”孟学平就说:“我写个地址给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卫民也一起来啊。今子,你说这样好不好?”
今子说:“当然。”
林文秋向他们告别。今子说:“我们不可以握个手吗?”又对孟学平说,“别看我们是朋友,可我们没说过一句话,不过,在陶家坞,就他对我好……”
“那真得感激你,你一定要来啊!”孟学平热情地摇了摇林文秋的手臂。
林文秋窘迫地握了握今子的手。
四、
今子的家,市政府宿舍。
林文秋一人来到今子家,今天这里气氛有些不谐和,今子一脸不高兴,孟学平则有些尴尬。
“文秋,不是对你,是他,心里不高兴,拿我出气。”今子象是对一个老朋友似的对林文秋说。
“今子,今天你不要生气了……,看在文秋的面上。”孟学平有点求和地说。
“文秋,——我才懒得和你吵。”今子回看孟学平。
“这样才好。”林文秋劝解道。
“不是,”今子说,“他要我当模特……”
“他学画?”其实林文秋已知道,只是随口。
“本校留校生,学西画,却教图案。”
“这为什么?”
“不为什么,论资排辈呗。就这,心里不痛快,反正现在也什么都不教了。他心里不痛快,拿我出气……”
“不会的……”
“什么不会的,他苦闷,我比他还苦闷呢,我现在……。哦,对了,我现在在一个拉丝模厂当工人,做研磨,是他爸搞来的。”
“我不就是叫她脱衣裳……”
“不要说了,难听不难听?”
“这有什么难听的,当模特,又不是不光彩的事……”
“你是不是要我脱光了,叫全校的人来画?”今子立即尖刻地反击。
孟学平就摇头。
“我陶今恃也是一个……,这种下贱的事我做不来!”今子很生气。
“今子,今子……”林文秋劝解道,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吵。
“你们是夫妻……”
“夫妻也不行!我不是不明白,就是做不到!”
“你看看,就为这,她和我吵。”孟学平无可奈何。
“我才不和你吵呢,”今子说,“我是要吵的人吗?你还不过来,陪文秋说话!”今子于是也持了一种和解的态度。
这是一幢三层红砖筒子楼,当时算洋房。今子家只十二三平米一间。
“大妹也在我们厂呢。”今子一边倒茶,一边说,“磨平面。”
“是吗?”
“你在我们这里吃饭吧?”
林文秋说:“不了,我只是来看看。”
“为什么不呢?家常便饭。——我来吧,”今子说完,站了起来,走了出去。
孟学平来陪林文秋。
孟学平和林文秋谈美术,谈文学,两人谈得很投机。
又一场景,徐卫民和林文秋。
“孟学平他爸?”林文秋问。
“老八路,市委常委,只是,现在在审查……。”徐卫民这人交际很广。
“你和他们熟?”
“当然了,”徐卫民海吹起来,“不过,也不,只和学平还可以。你认识今子?”
“她家和我家就两个村子,很近的。”
“是个好女子。”
林文秋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学平为了娶她,差一点和家里闹翻了呢!”
“哦,还有这事。”
“不过,他们好象并不好……,老吵架。”
“为什么?”
“不知道。”
又一场景,林文秋在路上碰到今子,两人一起走。
林文秋说:“听徐卫民说,学平为了你,差一点和他父母闹翻了?他对你真好。”
“还可以吧。”今子说。
“可你为什么老和他吵啊?”
“他这人,太要管我了,有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什么都不让我做,当然,是为我好。这我感激他,可我就是受不了。”
林文秋听到这样的话,就不知道该怎样来劝今子。
“你为什么问这个?”今子突然问。
“哦,不,不是,我怕你过得不愉快,我希望你过得愉快。”
“我过得很愉快啊。”今子说。
孟学平,今子,林文秋在郊区游玩,徐卫民也在,他们一起拍照。
孟学平拿一件衣裳披在正在摆姿式的今子身上,今子不要,两人又吵了起来……。
孟学平一和今子吵架,就来要求林文秋,要他扮演调解人的角色。
林文秋思恋着今子,他想着今子的面容,有些意绪难平。他拿起了笔,写下“假日车站”四字,然后疾书,是一首诗。然后,将它和所写的东西一起丢在床头。
一天,孟学平和今子偶过林文秋的厂子,他们就来看林文秋。林文秋不在,孟学平就走出来看工厂的风景,工友们则去叫上班的林文秋。
林文秋赶回来时,今子正有些冷淡地走出来,看见了他,就叫学平,说要走。孟学平忙说:“急什么,文秋不是才来?”今子说:“我有些不舒服!”见她不舒服,林文秋也不好挽留。这样今子他们就匆匆地走了。
林文秋怔住了,他翻了翻床头的那诗集,露出了一丝苦笑。
标语:反击右倾翻案风,今子的公公在疗养院接受批斗。
今子和孟学平恩恩爱爱地走在林荫道上,今子在以这样的方式支持着自己的丈夫。
孟学平对林文秋说:“今子是我一生最值得珍惜的人!”“娶今子是我孟学平一生最正确的决定!”
今子的妈妈生了未分化型乳腺癌,病故。
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庆祝粉碎“四人邦”。今子的公公官复原职,主持市革委会会议。
一年四季的景色过去。
又一年三月底,林文秋突然接到今子一封信,说很久没见到他。她要在二号清明前的那个星期天给奶奶父母上坟,那天,她希望能见到他,并希望他能给她带一把整坟用的锄头。
林文秋看着这信,看着只有今子一人的署名,疑惑不解。
五、
一个晴朗的天气,一个清明时节云低风和的日子。
樟树岭车站还是一尘不变,根他妈还是根他妈,她问林文秋:“坐车呀?”
林文秋说:“不,等今子,今子今天来上坟。”
“唉!”根他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叹息了一声。
林文秋就有一丝黯然。
今子是一个人来的,她很高兴。林文秋接过她手上的旅行袋,她看了林文秋一眼。然后向根他妈叫了一声:“根大妈!”走了过去。根他妈“嗳!”了一声,立即拉着今子的手,左看右看,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今子着一件淡灰色薄毛衣,一条浅青色长裤,一双布鞋,剪了一个齐耳短发,全然一个少妇样子。今子掩了嘴,笑了,有些不好意思,说:“根大妈,过后我来看你。”
他们朝陶家坞走去。
“怎么,学平呢?”
“我们不说他。”
“吵架了?”
“我们不说他好吗,等会,我会告诉你的。”今子脸上掠过一丝阴影。
他们来到一个山边(远处响起鞭炮声),这里有两个坟,是今子奶奶和父母的坟。一年不来,两座坟早已野草长满。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令今子看了伤心,今子的眼圈就红了。面对这样的场景,林文秋不知怎么办?就用锄头帮她整理坟堆。今子则拉开旅行袋,拿出祭物,把它们摆在碑前。坟堆上的杂草很快除去,又培上新土,于是两个坟堆又垒起来了。又砍了几根细竹,这时今子拿出纸幡,挂在细竹上,在两个坟头各插几枝。一切做好之后,今子后退了一步,站在墓碑前。林文秋替她点上香烛,炸响鞭炮。
鞭炮响起,硝烟弥漫……,纸幡在一缕缕的风中零乱地飘动……。想到惨死的奶奶、父亲,想到艰难的母亲,万千悲痛涌上心来,今子一下子扑向墓碑,抱着墓碑,放声大哭起来。看着她这痛不欲生的样子,林文秋心如刀绞。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死者已已矣,总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林文秋知道今子的心苦,只是不知道这苦是什么?
烧纸钱时,今子一个膝盖顶着地的在那里又伤心地流起泪来,怎么劝也劝不住。看得出,这次她是在为自己的人生伤心,林文秋就问她:“和学平吵架了?”
今子点了点头。
“为什么?”
“和你说什么呢,为孩子,你不懂。”
林文秋沉默,他没有结婚,自然不好问。
“就为这,也不能不来祭你父母啊?”
“他有事,赶一个画展。”显然,今子在掩饰着什么,因为,这不是理由。
“文秋,去年恢复高考了,”今子转移了话题,说,“我本想考大学。”
“这好啊!”
“可学平没让我去。”
“为什么?”
“唉,不说了。”今子不想把她和学平之间的矛盾说与林文秋听。林文秋也不知道她和学平到底有什么矛盾,只是觉得学平对她有点宠爱过度,宠爱过度就有点象霸道。今子不是骄宠的人,就不得不委屈自己来牵就他,这林文秋就更不好问了。
剩下的时间,今子要林文秋陪她在这故里走走,看一些她不知道的风景。这容易,今子在这里其实那里也没去过,她只寒暑假来一来,不大出门。今天这样要求林文秋,自然是心里郁闷,她想看油菜花,林文秋说,可以看,不过昨天下了雨……,今子就说:“哪就看采茶吧?——哦,还是不去,不去。”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林文秋知道她已经知道了这乡下的风俗,立即应声道,并乘机解释起那一年的事来,“还记得吗,有一年,在车站……”
今子笑了起来,说:“不要说了,我知道了,那时年青……”。她对这事记得很清楚。
“这样吧,我们从这边过去,那里有一大片油菜田,我们穿过那油菜田,到那边的山野,采火焰花。”
“什么火焰花?”
“——真好,映山红啊,好,我们去采映……火焰花!”
油菜正在怒放,一片明黄黄地看不到边,在这春阴的天气里,油菜地倒比天空还明亮。今子延着一条田埂跑,在无边的花海里。油菜快有她人高了,看得出她很尽兴。等到她跑出油菜田,她那淡灰色的薄毛衣和浅青色的裤子上全是一个个黄点:“哦哟,这是什么呀?——花粉!”她叫了起来,接着就笑了,惊讶得很。
那天,他们采了一下午的火焰花。
林文秋还带她去看一壁陡峭悬崖,一两百米高,刀削过一样,今子捧着一大捧的花抬起头来看。黝黑的悬崖上,雄鹰在盘旋,天空特别高远。崖底的风象流水一样,有感触地梳理着一切,也梳理着她,原来她只是一个这么小的女人。悬崖下是一条春水,在这悒郁明亮的酿花天气中,就象一首诗,黝黑得令人心悸,悒郁得象一段沉重的心底。
正玩得高兴,突然,今子说:“我要回去了。”也没有什么解释。于是他们就朝回走。
六、
到了车站,今子有点意外地说:“啊,怎么就到了,我还以为很远呢。”
班车还没来,根他妈拉着今子说话,问:“这么多年了,怎么也不要个孩子?”
今子说:“还年青呢,不忙。”
班车来了。
今子对林文秋说:“好了,今天,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是我朋友,不谢了。下次,我带学平来,你要不嫌烦,还要你带我们玩……”
车子开动,尘土飞扬,今子从车窗伸出头来,远远地看见林文秋站在那里向她挥手。今子流露出一丝感动,又有些怅惘,意绪难平。
“怎么也不要个孩子?”车窗外的风景一一闪过,她想起等车时,根他妈问她的话,表情露出一种痛苦。
她似乎不愿意去想。
今子家里。
“你干嘛让妈给我请长病假?”今子有些不满的问孟学平。
“你看看你这身体,”孟学平说,“不请长病假行么?”
今子一做事,孟学平就叫:“放下,放下,——我来!”
今了只得无奈地苦笑。
孟学平什么也不让她做,使得今子痛苦。孟学平这做法使今子感到了一种胁迫,他这行为是一种强制,在这种爱下,今子感到自己象掉进了水里,要闷死了。今子就冷语夹暗箭地,处处不顺孟学平的心地来反抗。这又使孟学平不痛快,两人吵起来。
孟学平尖刻地说:“我这样待你,你还要怎样?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他甚至说,“你们女人,谁对你们好,你们就爬到他头上。对你们女人,就是不能太好!”
听到这种话,今子受不了,也出语尖刻:“就你家这德性!”
一听这话,孟学平也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说:“你是说爸?”
“他自己说的:‘他参加革命是碰到的,不是想参加共产党。三八年,他投军,投国军,结果投了一个什么青年教导队,那知是党的外围组织,’他说,‘碰到了,撞了大运。’”
今子一时气急,就这样说出。
孟学平就不响,过了一会,甩手离去。
又一场景。
今子:“去年你不让我考,今年我一定要考?”今子在对孟学平说。
“可你这身体……。”孟学平有点为难地。
“我总不能一直这样吧!”
“反正家里条件好,养得起你。”
“我不能就这样一直让你养!”
“这不是很好吗?”
今子说:“不,今年我一定得考!”
“不行!”
今子恨极,说出了这样的话:“你是在以爱的名义扼杀我!”
七、
樟树岭车站,林文秋一人在徘徊。
春花秋月的过去,今子不再回来。林文秋来到他和今子到过的地方,睹物思人。
樟树岭车站前,公路正在铺柏油马路。
林文秋在寝室里,抽烟,有点颓废地思念着今子。
那片清明前的油菜田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那一片灿烂的火焰花,那个云翳布满的春阴天气……,那在油菜田里奔跑的今子,成了他永难忘记的回忆。
他猛地掐灭了烟头,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似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他和今子不再来往。
生活的浪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汹涌,到处是展开的工地,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
林文秋忘我的投入到工作学习中,报纸上出现了他的文章。
今子又在和孟学平争吵。
周晓洁出现,林文秋和周晓洁散步在花前月下。
婚礼,林文秋和他厂里的医生周晓洁成了家。
八、
一天,林文秋周晓洁回家看爸妈,在车站听根他妈说:“今子离婚了。”
根他妈说:“好象是今子不好,两口子吵得挺凶,孟学平不答应,今子却坚持,结果,法院还真是判了。”
林文秋就去见今子,今子的模样很憔悴,不象是一个挣脱了羁畔,获得了心灵舒展的人的样子。林文秋看得出,她在极力压抑着心中的悲伤,强作欢颜地来面对他。他立即感到,事实的真相可能并不象表面呈现的那样,就问为什么?今子的回答:“只能这样!”
“……他在以爱的名义,剥夺了我的一切,以及我的生活情趣和理想。我感到我要窒息死了,再不离开,就活不了了!”今子几乎是喊着地叫了出来。
“我怎么看不出来?”
“他怎会让你看出来?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今子似乎下了狠心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就不要问了,难道你还要看到我再受到伤害不成,让我再看到他那道貌安然的样子,在我的心口上再戳上一刀不成?——孟学平是我最恨的人!你不要听他说,那全是假的!我是决不会回到他身边的,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不要再掺和到我们中间来了。”她说完这句话,就用手捂着脸地呜呜地哭了起来。
见到孟学平,孟学平的样子也让林文秋不能理解,因为他好象被这次的离异击跨了,头发胡子拉杂,双眼充血……。林文秋怎么也不明白,这孟学平怎么能和今子所说的那个孟学平连系得起来……。
孟学平说:“不就是第二次高考嘛,你看她那身体,还能高考?假如是你,你会怎样做?再说,我什么时候管过她?你不知道,她这人后来有点神精质,动不动就哭……,我妈就带她上医院。就是太依顺着她,把她惯得没边了。前段时间,无事找茬,动不动和我吵,非离不可,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我都让着她,就是格守一条——不离!我不是什么都依着她吗?她反而得寸进尺,——你看看她那身子,一吵就病。那时,吓死我了。实在没办法,难道要把她逼死?看着她那日异憔悴的样子,我心痛,只好咬了咬牙……。”
“我还要去找她,等她平静一点以后,再去找她,我一定要复婚。这一段日子,文秋,你要帮我好好照顾她……,劝劝她。”
林文秋对孟学平说:“你们这事,我管不了。”又对今子说:……,今子马上脸一翻:“你是不是帮着孟学平来坑我……?”
林文秋无可适从,星期天,常一人回樟树岭。
每次下车,向根他妈问一声好;每次候车,又和根他妈说说话。根他妈的女儿大妹在今子厂里,其间,听根他妈说:“孟学平常找今子,要求复婚。今子要不不见,要不就斩金切铁……没有挽回的余地。”
“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根他妈叹息着说。
孟学平反复来找今子……,几近疯狂。
林文秋想劝阻他,孟学平不同意。
林文秋又去劝今子,今子说:“他再这样,我就离开这里。”
林文秋吃了一惊,忙说:“不,不,千万别……”
“真叫人活不下去了!”今子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有点伤心之极。
林文秋就楞住了,又赶快去找孟学平。
但这事却成了事实,不到一个月,——今子辞职了。
那天大妹来找林文秋,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今子留职停薪,离开了拉丝模厂……。”
“这,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
“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她这事做得很机密,我们厂不是经济效益不好吗?允许职工留职停薪。星期天回厂,才知道她已走了。厂里传着这件事,说她拿了陶老师的补发工资,一大笔钱,到广州去了。
“陶唯一?胡诌!陶唯一六六年就死了,能补发几点工资!”
孟学平到处寻找今子。
林文秋和孟学平相对饮醉,他开导他,说:“不如算了,今子对你真的死了心,她恨你。”孟学平听后一怔,他没想到今子这么绝情,就猛饮酒,最后哭了。当他听到林文秋说,今子拿了陶老师的一大笔补发款去了广州,就用充血的眼睛看着他,不由得哈哈地大笑起来。
“没想到她是这样一个人!”他恶狠狠地说。
“也许,她真的过得很好呢。”林文秋说。
“我就不信,我会活不过她!”孟学平这次是真的死了心,不过,孟学平又说,只要她陶今持过得好,将来有个好归宿,对我孟学平怎样都不计较,就怕她过不好,我就很伤心……。
林文秋忙说:“不会的,不会的,今子又不是没本事的人。”
“也是。”孟学平怔怔地说,“如是这样,就只有真心地祝福她了,唉!”他长叹了一口气,“只怪我和她没缘分……。”
时间的过去,孟学平的感情慢慢平复。
孟学平的爸妈找孟学平谈话,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应该成一个家。”
孟学平开始不听,后来就沉默,继而叹了一口气。于是孟学平的母亲为他张罗开来。八九年孟学平就成了新家,有了孩子。如今一家人其乐融融,过得很好了。
九、
一天,如今已在报社当编辑的林文秋突然接到今子的电话,忙问她在哪里?她在那边说:“不告诉你,要是告诉了你,又要告诉学平去,让我不得安生。再说,我也有了对象,他又成了家,你把我在某处的事告诉他,就不道德了,是不是?哈哈……”电话那头响起了她轻盈快乐的笑声。从这声音里,林文秋感到了她的活力和快乐。不过林文秋也感到惊讶,她怎么知道孟学平成了家呢?就问:
“你怎么知道学平成了家?”
“这你就不要问了,我还要祝贺你当了编辑,实现了你的理想。”
“怎么你都知道?你来过这里?”
今子那边已挂上了电话。
林文秋陷入了沉思。
林文秋和孟学平。
孟学平问:“还没有今子的消息?”这次是他在问林文秋,令林文秋感叹。
孟学平见林文秋怪怪的,就问:“是不是在怨我?”
林文秋说:“这事又不能怪你……”
“可能还是我的不是。”孟学平说。
“为什么?”
“我不该那样去逼迫她。”
“你现在已成了家,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也是,但我只是怕她过得不好!”
“她过得很好。”林文秋一下失了口。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你知道了她的消息?如果你知道了她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你要相信我,我成了家。但我就是想知道,她过得怎样?只要她过得好,我就一辈子就不想她,也不找她,这,你一定要相信我。”
听他这样说,林文秋想了想,就告诉他,说:“是的,她给我打过电话。”
“那她在哪里?”
“这我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过得很好,而且有了对象。”
“真的吗?这太好了,这样我就真的不为她担心了,谢谢你!哦,这真好,我们的今子有了对象。下次,再给你打电话,就告诉她,说我孟学平祝福她。告诉她,叫她回来,夫妻不成,还可以做朋友。文秋,你说,是不是?”
“当然!”看着如此高兴如此孩子气的孟学平,林文秋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他喃喃自语道:“这是为什么呢?”
十、
清明,林文秋常代替今子来看一看她的父母,今年也是这样。他下了公交车,樟树岭车站已不是昔日模样,首先它前面的公路已不是那一条窄窄的柏油马路,如今它是非常宽阔的柏油马路。车站也很气派,原先的风雨亭还在,只是更加破败,但不萧瑟。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根他妈换成了大妹。如今大妹把这风雨亭改成了一个小卖店,卖些糕点、可乐、雪碧之类,这店也就越开越红火。
林文秋望着这虚无飘渺的故乡,露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
戴着黑纱的大妹看见林文秋,着急地招手:“文秋,文秋!”一副急死了的样子。
“咦,怎么是你?大妈呢?你这是……?”
“为我妈,她……老了!”
“哦,真对不起,那你?”
“我下岗了。不,不是,不说这个,今子来了!”
“什么?——今子?你说今子来了?她在哪?”
“走了!”
“走了?”
“前几天来的,看她爸妈……”
“你是说,她祭奠了一下她爸妈,就走了?一个人?”
大妹描述那天的情景,说:“就今子一人。见到今子时,有点认不出来,人瘦了。说是成了家,那一位不能来。”
“成了家?”
“是的,她是这样说的。但不象,我看象撒谎……。好象混得也不好……,你知道,城里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她虽精心打扮,可那种小地方的样子……。我劝她多住几天,和大家见个面。她说很忙,再问,就叉开话……。后来公交车来了,她就急匆匆地上了车,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知道她活得很艰难……”
陶唯一夫妇和今子奶奶新整的坟前,除了几竿纸幡依然在春风中零乱地飘动,祭品已被拾荒人拿走,因而显得既零乱又惨淡。
“唉!”:站在坟前的林文秋叹息了一声。
“她是在逃避我们!”随他前来的大妹说,她把小店交给她丈夫管。
“嗯,也在逃避学平。”林文秋说,“可这是为什么?想不出啊。”
“会不会是来看她的父母奶奶?好几年没来,离得远。”
“当然,也只能这么解释,不过,这事不能让孟学平知道。”
“这我知道。”
一阵风来,一片落红漫天飞舞,这是这天地间的至情,在无尽致地喧泄,席卷过来,象要把这坟前的一切拥去,述说着这人世间的永远循环不尽的不幸和哀伤。
十一、
林文秋在林荫道上碰到孟学平。孟学平带着孩子,看到他父子俩其乐融融的样子,林文秋不敢把今子曾经回来过的事对他说。
孟学平谈到今子。
林文秋沉思了一下,下了决心地说:“今子如今过得很好,她已成了家……。”
“是吗?”孟学平显出了一种放了心的轻松,兴奋地说
“如果今子过得不好,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现在……,哦,这真好,太好了!我们的今子成了家!”
他们不再谈今子,孟学平谈他的创作,谈他参加的新锐油画展,林文秋真心地祝福他。看着孟学平离去的背影,——你看他,他突然抱起了孩子,把他举得高高,旋转着,快乐地大声朗笑着,几乎是飘着地走远了。他再也没有了那一份牵挂,也没有了那一份对今子的负疚。
林文秋呆在那里看着他远去。
可这是为什么?
他想起大妹的话:“她那小地方的样子,……她活得很艰难。”
林文秋对周晓洁说:“如果大妹的话不谬,那今子可能就没有离开过这里,她一定躲在此地某一个偏远的小城镇里,默默地躲避着我们,关注着我们,直到事情有个圆满的结束。哪这事又是什么?”
晓洁说:“会不会是要看到学平成家,不让学平再来纠缠她?”
“你怎么也知道?”
“说什么呀?从你们的言辞中,我也知道一些啊!”
周晓洁对林文秋和今子的事早已知晓,她早就看到过他那首《假日车站》,知道他喜欢今子。她曾对林文秋说:“看样子,今子也曾喜欢过你。”林文秋说:“这不可能!”周晓洁就说:“真正的爱有时是看不到的,但我却看到了人世间真爱的化身——今子!”
“你不会怪我吧?”
“看你说的,我相信你。”
“我想了解今子的生活,可到哪里去找她呢?人海茫茫。”
晓洁看了看丈夫,想了想,才说:“这还不容易?如果大妹的判断不错,这里又有她的照片,只要把这事对大妹说一声。她那里人来人往,只要上点心,问一下……,不就解决了。”
“对呀,这,我怎么没想到!”
今子远在五十多公里外的A县某镇,在那里开了一个小书店,这,真不幸!
林文秋对周晓洁说:“我想去看看她。”
“你呀,书呆子,这怎么可以,你去看她,不白费了她这一番心思?你的猜测可能不错,她一定有什么原因,要让孟学平解脱,这一去,又要让她所作的努力落空,你还要她怎样啊?还有,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孟学平……,也要吩咐大妹……。”
“这我当然知道,我已这样告诉她了。”
“我是这样想的,”晓洁想了想说,“她不是不认识我?这样吧,我代你走一趟,她反正不认识我,我可以直接到她店里去,和她聊聊,也可以有个了解……”
“这主意不错。”林文秋说。
星期天一早,周晓洁去了A县某镇。
十二、
A县某小镇。
尘土飞扬,窄窄的一条街,商品铺到街中心,混乱而繁荣……。
周晓洁没怎么找,这里除了一家新华书店,就今子一家书店。周晓洁去时,今子正坐在书店右侧的边柜里,还有一个小姑娘(翠敏),是店员。
今子老多了,精神也不集中,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象五六十岁。晓洁进了店,装着买书。今子不来理她,只是看了看,又低下头看她的书。小姑娘也坐在那里百无聊赖。今子不象一个做生意的人,不大懂。比如,晓洁故意挑了一本博尔赫斯诗选,是那种三卷本中的一本。今子就说:“这是不零卖的,要买买全套”。晓洁说:“我不喜欢博尔赫斯的小说,只喜欢他的诗。”今子就站起来把晓洁的书收了,放到书架上去。晓洁说:“老板娘,你不好好看看,这可是一本单本啊。”真的,这虽是三卷本中的一本,却是一本单本。今子很奇怪,看了看另三本博尔赫斯,似乎有点不懂。问小姑娘,小姑娘也不知道,怎么会出现一本单本?这一点,晓洁也不懂。今子又翻了翻书架,转身时又回头看了看,实在是不懂,就拿了书走进边柜来。“交钱。”她说。
趁着这机会,晓洁故意无话找话,说:“老板娘,看你真不象做生意的,做生意的,那有你这样生硬不知变通的。现在卖书很赚钱啊,你这里怎么这么冷静?”
“你以为卖书赚钱啊,”今子说,“你哪来的?”她问晓洁。晓洁说省城来的。“那当然不同,”今子说,“你以为这是省城,省城看书的人多,这里有谁看书?”
“既然这样,你不可以改行吗,象他们,”晓洁是指旁边的小店。
今子说:“算了吧,折腾了一辈子,不想再折腾了,能过得去就算了。”
听今子这样说,晓洁感到很凄凉。她装着打量书店的样子。那是一间很小的书店,十来个平米,在打量的时间里,晓洁突然有了主意,决定再进一步打探下去。就装着接着上面的话来说的样子:“哪你先生也同意?”
“什么呀,我姨妈还没成家呢!”小姑娘说。
这话吓了周晓洁一跳,她真的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她记得林文秋告诉她:“今子告诉我,她有了对象,成了家”。怎么现在又没成家?好在晓洁正在看架上的书,掩饰过去。她又挑了几本书,交钱时,故意装出开导的样子,说:“我看你,不会做生意,现在那有卖这种书的,不是新潮思想,就是纯文学、西方名著……。城里现在在卖琼瑶、新式武侠……”
“这么大了,也不成个家?有孩子吗?”晓洁故意装着一点也不知晓的在继续。那知,这话一出口,晓洁就有点后悔,她记得林文秋告诉她:“今子非常敏感。”真的,这话一出口,今子就抬起了头,疑惑地看了看她,没有再理会。
晓洁就知道,不能在这里呆了,匆匆交了钱,回来。
十三、
“今子真可怜!不仅没有成家,而且过得极其艰难。”周晓洁对林文秋说,“只是她为何要这样折磨自己?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你能想出为什么吗?”林文秋问周晓洁。
周晓洁想了想,问他:“你说,她和孟学平常吵架?”
林文秋说:“是啊!”
“今子告诉你,吵架是为了孩子?”
“是啊!”
“这就对了,难道今子不会生育?”
“不会的,她怀过的!”
“怀过的也不一定还能怀上,我想这事一定出在这上面,一定是今子经过什么变故,不能生育了。这事只有她一人知道,学平又是独苗。她爱学平,不忍心看到他为此痛苦,更不忍心看到他孟家断后。而这事,又不能让学平知道,一旦学平知道了,这事就做不成。所以她只有装着和孟学平决裂的样子,让孟学平蒙在鼓里,而让一切的痛苦都让她自己一人来承担。她还了孟学平自由,且不让他留下一点精神负担……”
林文秋想了想,说:“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解释?”
“哪现在怎么办?”他又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帮她?”
“这不行,”晓洁说,“不是我不帮,是我们帮不了。只要我们一出现,她目前这样的生活也就保不住了,象她这样的人,会做得很决绝。”
“那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好人自有好报。不过我们可以找徐卫民来了解一下……”
“徐卫民?”
“对,徐卫民,他不是和孟学平好吗?你说他好象也很喜欢今子,今子离异后,他就不大和孟学平来往,这不正好。不过这事不能直问,徐卫民这人嘴巴不牢,要是知道了这事,说不定就捅给了孟学平……”晓洁又想了想,说,“这样吧,让徐卫民来我们家喝酒,喝酒的时候,什么也别问,装着随便问到今子,就听他海吹……。”
酒半酣,徐卫民海吹起来,说自己又认识了某某名人,某某局的局长公子,又某画家,最后说到文艺学院编导系的某教授。他说:“现在文艺学院也不在原地方,搬到郊区去了。”
“哦唷,文艺学院呀,”周晓洁见机,立即接话,说,“不是今子住的地方吗?”
“是啊,说到今子,才想起,”林文秋说,“如今这今子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徐卫民就很伤感。
又说了一会儿话,徐卫民来向他们打听今子。晓洁狡诘地说:“你又和今子不熟……”
“我和她不熟?”仗着酒意,徐卫民一副豪气干云的样子,口无遮拦地说,“我和今子够铁的了;我曾帮助过她,比如买彩电……。”
“不会吧?”晓洁说,“要是这样,今子怎么就没在我们面前提起过你?”
“什么呀,”徐卫民立即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他说,“今子什么事不找我?今子他们看病也找过我,要我帮他们找个好医生……”
林文秋和晓洁听到这话就不敢响,只装着不在意的样子,静听他说。
“他们连放环这样的事都找我……”
林文秋正想开口,晓洁立即作了个示意的动作,于是他们不再谈今子。
“你为什么不让我问?”徐卫民走后,林文秋问周晓洁。晓洁说:“没必要。”“为什么?”“事情已经清楚。”“怎么……?”
“我是医生啊,今子夫妇为放环,找徐卫民。放环为什么要找徐卫民?这只能说,这环不能放,要放环,到处都好放啊。徐卫民也混蛋,给她找了那么个医院,某某医院,那是什么医院?跟野鸡医院差不多,一定是放环出了问题,感染了,损伤了,或者是后面出了事,或者是又怀了孕。反正,今子肯定是出事了,为这,她不能生育了!——这不会错!”
林文秋和周晓洁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之中。
画面:一边是今子在小镇卖书;一边是孟学平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着。
孟学平油画展,鲜花,他获得了成功。
有些福态的孟学平在安逸地画画,他妻子温情地看着他,给他倒上一杯茶。
有些苍老的今子在书架前整理书籍,异常憔悴。
十四
字幕:十年过去了。
林文秋也有些老了,这天,他和周晓洁回到樟树岭。
樟树岭车站又有了大变化,原来的风雨亭已被大妹拆除,她在原址上盖了一个整洁的红瓦小平房,生意也越做越好。这次,当林文秋问起今子时,大妹不无揪心地说:“回来了,上个星期吧,认不出来了,老了许多。人也瘦得不成样子,脸腊黄腊黄,她叫我不要告诉你……,也不让我打电话,还问了你的电话改了没有?我告诉了她。那天,她在她父母坟前呆了一整天,我怕出事,叫老头子去看看。老头子说,她在她父母坟前哭,哭得很伤心。我总觉得她好象有什么事似的。等车时,就问她。她又笑着说:‘没事’。可我看得出来,她一定有事,好象是在向她父母告别似的,现在想起她那样子,都感到可怕。”
林文秋和周晓洁听了就感到揪心。
回到家后,林文秋对周晓洁说:“是不是去看一看她?”“我也正这样想呢。”周晓洁看了看他,接着说:“这次,一起去吧,当然,依然不让她知道,只是站得远远地,看一看就是了,如真的没什么,也放了一颗心。”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们前往A县某镇。
某镇并不象周晓洁那次来时那样尘土飞扬,而是有点整洁了。新楼房也盖了许多,不过依然显得破败。
他们朝今子的书店走去。快到今子店时,晓洁拉着林文秋避进一条小巷,朝今子书店望去。今子不在,店里一个姑娘在照看。这小店在这大街上,显得不谐调,特别破败,歪斜斜的要倒一样。
“那是她的雇员,”晓洁说,“上次来时,还是一个小姑娘。”
“今子怎么不在?”林文秋问。
“我怎么知道,这样吧,我进去看看……”
“我也去。”
“这怎么行,万一她出来了呢?”
“这样吧,我就从她门前走过,二十年了,就是出来,哪能一眼认出?”
周晓洁进了那店,林文秋装着一个过客,从店门前走过。来到门前,瞟了一眼,见今子不在,就站住,抬起头来看。那女店员朝他看了看,林文秋就走过去。过了一会,周晓洁出来,找到林文秋,对他说:“想不到,十多年过去了,小姑娘好象还认识我,真奇怪,不就是一面之交。”这时,那女子进去,一会儿又出来。紧接着今子也出来,扛了一捆书,放下,叫那店员拆开放上书架。她自己又进去,一会儿,又扛了一捆。今子人很瘦,却精神,也很开朗,不象有什么事故。看到这里,林文秋和周晓洁难过地低下头,默默地走了。
十五、
秋叶飘飘,春花怒放。这一天,今子突然给林文秋打来电话。
林文秋不在,周晓洁接的电话。周晓洁在电话里到处找林文秋,见了面对他说:“今子可能碰到了事,叫我们去看看她。”
听晓洁这样一讲,林文秋就觉得不对,问:“今子主动找我们……。”
“嗯,是的,我答应了她,”晓洁说,“我说,星期天我们一定去。——她不会出事吧?”晓洁又说,“一接电话,问她是谁?就说:‘嫂子吧?我是今子,见过面的。’这话怎么讲?吓了我一跳,她怎么知道哪是我?我还以为我做得很机密呢。”
“她给我留了电话。”晓洁又说。
但这个星期天林文秋他们没去,周晓洁的妈妈病了,他们忙着送她住了医院。林文秋打电话告诉今子。电话那头,今子很失望,虽然林文秋在电话里一再问她有什么事?也一再向她道歉。但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失真,不大象是今子的声音。
“我这里实在是脱不开身,晓洁的妈妈好些,我们一定去……”
“哦,那好吧,不要紧的。”今子总是替别人作想。
晓洁的妈妈出了院。林文秋打电话通知今子。可这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他和周晓洁觉得情况有些不妙,立即分头请假。
他们匆匆赶到A县某镇今子的小店,只见店门关着,摆了几个花圈,上写陶今恃千古之类的挽联。一敲门,那姑娘出来,看到林文秋他们就哭了。
“怎么回事?”周晓洁拉着姑娘的手焦急地问。
“等一下,宾仪馆的车要来了,刚来电话,说要火化,拉花圈。你们要是再不来,就见不到了。”果然没等十几分钟,宾仪馆的车就到了。他们把花圈搬上车,这姑娘锁了门,他们就上了车。
姑娘自我介绍:“我是今子的远亲,叫翠敏,我妈妈也来了,在宾仪馆。”
“……也是想等你们来看看,我妈妈一直在要求他们……。姨妈是前天故去的,”翠敏叫今子为姨妈,其实是表姨妈,“可她一年多以前就查出了左乳乳腺癌,在省肿瘤医院开刀化疗了半年,上两三个月右乳房又痛起来,一复查,才发现已经转移。姨奶奶好象也是这个病……”
“为什么不去……?”
“去了,半个多月前拉了回来,说是不能治了……”
这时林文秋才知道,为什么半个多月前今子给他们打电话,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
想到今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那样地凄凉,无望,他和周晓洁的心都要碎了。
“她没有留下一句话吗?”
“有,给你们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她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几天。不在这,等一会回来,交给你们……”
今子躺在玻璃棺里,周晓洁、翠敏和翠敏的妈哭了,林文秋默默地咬着嘴唇。
今子很瘦,显得有些苍老,颜面有些舒缓,就象放下了一些重荷,再也没有了一点遗憾一样。也许化了妆的缘故,依然象活着。
“姨妈说:她只要我们四人来为她送行,”翠敏说,“她说,她要永远地向这个世界告别,而且不再回来。”
画外音:质本洁来还洁去……
林文秋感到一阵悲怆,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流下。
十六、
今子的房间,玻璃台板下压着几张照片,那是林文秋和孟学平今子在一起时照的。看着这几张照片,林文秋似乎有点明白,他想起,那一次他和周晓洁来看今子,或许就是那一次,翠敏看到了他,由于经常看到这些照片,所以认出了,也就有了今子抗着一捆书的出现。今子是在向他们掩饰,不想过早地让他们来为她担心,也不想再搅乱了孟学平的生活。
这想法得到了翠敏的证实。
“……那一次伯母的出现,”翠敏说,“姨妈有些猜疑,说:‘今天这人奇怪,怕是有目的的……’她的事我知道,叫她不要乱猜,她也没说什么,所以记住了伯母。你们第二次来后,我还就此事问过她,她说,既然你——伯母——不想让她知道,她就相信你们不会把她在这里的事告诉姨父。她是为姨父才离开姨父的,”翠敏依然叫孟学平为姨父,“她不能生育了,姨父又想要孩子,姨父的妈妈又求过她,她只有忍痛离去……”
“还有这事?”林文秋想起了,有一段时间,孟学平的妈妈是常带今子上医院。
孟学平对林文秋说:“我妈常带今子去看抑郁症。”看样子是他妈欺骗了他。
“她不能生育了吗?”
“不能了,姨妈讲过,开始是年青,嫌烦,不知道天高地厚。谁知上环后又怀上了,做了人流,出了问题,就再也不能怀孩子。姨父的妈妈就求她,看在他家独苗的份上,离开姨父。她没有办法,只有同意……”
“那孟学平妈妈……?”
“姨妈说:‘不怪她,是她自己要这样做的。’并说,她要求姨父妈妈也别让姨父知道,否则这事就做不成……。”
“……姨妈常看你们的照片,所以那次我认出了你,但不敢肯定。就进去对姨妈说,姨妈一听是你们,立即扑向门前,不过马上又站住。你们真没看到,当时她浑身都在发抖,然后就叫我装着没事一样出来,自己就抗起一捆书……。”
“后来转移了,不行了,她已灰心到了极点,常看姨父,抚摸着姨父的脸。看到她那样子,我就流泪。她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别把她的事告诉姨父,让过去了的就永远过去,‘否则她这一番心思就白做了’她说。……”
“那她最后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只叫了一声‘学平……’就咽了气。”
“喏,这是她给你们的信。”翠敏说着这话,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交给早已是泪流满面的林文秋和周晓洁。
十七、
画外音:
文秋、小洁:
看到这封信时,我已远离了你们。按说,在这样的时候,我不应该再来找你们……
虚无飘渺的陶今恃在对林文秋周晓洁说:“本想就这样一了百了,但你们两次来看望我,使我想了也不能了,我不能无视你们的友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次,我非常珍惜,我很想好好的过完这一生,想拥有自己的幸福。当我发现我将做不到这一切时,我就想把我所希望的给与我所爱的人。
樟树岭车站前候车的陶今恃,她在静静的看书。
“爱,只能是一种奉献,我还能有什么呢?
如果我的爱使我爱的承受者感到悲伤,感到内疚,那就违背了这爱的初衷。
我想带走它,只是,我已无法将她收回……。”
陶今恃和翠敏在书店内。
陶今恃在对翠敏说:“关于我离去的消息,你要告诉他们,不要透露给学平,永远永远。尚若他问起我,就说我过得很好。过了一段日子,就说和我失去了联系……,
翠敏:“不要这样。“
“是我要斩断这一段情愫……。”今子说。
陶今恃出现在她父母坟前,对林文秋说:
“我已为我奶奶、父母新择了一块墓地,在青源山公墓。”
大妹在打电话:“村里要将土地卖了,房地产商要求有主墓地全部迁葬,否则将作为无主墓夷平。”
今子焦急地往来于两个墓地之间。
“后来,自己实在精力不济,时限又不紧,就没办完。现在只有转求于你们和小敏,把我和我父母奶奶合葬……。这样,学平将永远不会知道我的去向,我做到了,让爱这柄双刃剑不再能伤害到他。”
今子最后的时辰,她躺在床上对翠敏说:“迁葬公墓后,就对他们说,不要再来看我了,包括你。”
“不!”翠敏叫道。
“你还我以自由好不好?”
“不,我不,我又不认识姨父,不会让他知道的……”
林文秋周晓洁站在飘忽的今子床前,今子对他们说:“也许,你们以为我这一辈子过得很惨,过得很不幸,不,我说一句心里话,这样的时候,我无须掩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名誉?是地位?全不是,人所追求的是爱,是有人,那怕在千山万水之遥,对你的思念。这是我们人类最珍惜的,我得到了。我知道学平和你们一直在牵挂着我,我获得的是如此之多,我夫何求?”
泪水沿着今子的面颊流下来。
一望无际的油菜田,今子向着它奔去。
“还记得么,有一年清明,祭奠过我父母之后,你带我疯玩了一个下午,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
歌声:“春水弯弯、弯弯春水……”,
“我是那么放肆,大胆地向前奔去,那么一大片看不到边的油菜田……。”
今子向着油菜田深处奔去,虚化,然后飘向天空,宛如一缕云,无限留恋地回望人间。
画外音:“我将带着这美好的记忆走向天国,走向我心中的油菜田……。”
“别了,我所爱的人!”
十八、
樟树岭车站。
这是一个夏季,阴云不开的天气,大妹的小卖店还在。
林文秋问大妹:“生意还好吗?”
“好着哪,只是,也开不了几天了,”
“为什么?”周晓洁不解。
“造别墅哪,这些该死的房地产商,逼得我们都活不成了!”大妹骂道。
“难道……”
“别听她的,拿了五十万哪!一辈子都吃不完。”一乡里人说。
“五十万怎么啦?我恨死了这些房地产商!是他们,把我的家都毁了!”
远处茶山上,推土机,挖掘机尘土飞扬地在轰鸣,重型大卡在穿梭,打桩机也竖起来了。
这乡村,在现代化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睹物思人,林文秋周晓洁怀念今子。
晓洁说:“现在,再也没有了今子这样的女子了。”
大妹的小店开始被拆除。
青源山公墓。
林文秋他们把今子的后事一切都了了。这时,翠敏对他们说:“姨妈在最后弥留之际,一天,清醒了些,叫我拿火。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就拿打火机。她说:‘打着!’。我就给她打着,她从贴身处拿出一张纸,烧了。”
“什么纸?”
“不知道,好象是一首诗。”
“诗?”
“我不大知道,好象是。”
周晓洁看了看林文秋,示意他不要再问。林文秋好象有些明白,就不敢响。
回到家后,周晓洁对林文秋说:“我说了,今子曾经爱过你。”
林文秋故作不信地说:“这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周晓洁说,“你是她的初恋,而且刻骨铭心。因阴差阳错的使你们产生了误解,分开了,她嫁给了孟学平。嫁给孟学平之后,才发现你是爱她的,但她是今子,她当然不会去做出出格的事来。但爱无法终止,这就显示在她的生活中,和孟学平无法做到和谐,所以他们经常吵架。孟学平又对她那么好,所以她始终保持着对孟学平的爱,一直到死叫的人依然是学平,唉,今子,今子啊!”晓洁叹了一口气。
“你为什么要把这说出来?”其实林文秋已明白。
“我不想把她从你心里抹掉,这么好的今子,我希望她能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林文秋轻轻地吻了吻周晓洁。
一个人坐在窗前,拿出他的诗集,打开,翻到《假日车站》:
歌声:
一片
消失已久的回忆
蓑败的夏日在浅灰色的绿色里
太阳 努力偏着头
打着它的歪主意
神秘的水渍 漶漫着未来城市的影子
天空在虚无里
公交车在荒诞里 一些
陈年烂谷子般地锁事
撒满了人们川流不息的旅程
多年不见 邻村的小妹妹
当年的那一个我所爱恋的女孩
你是否还能与我携手
再一次地走上这个站台
今子从那樟树岭山野中走来,依然是那样梦幻般地飘着,然后走向远方。
在远方,她回转身来,向着人们,露出她那温款的一笑……。
专业定制代写小品、相声、话剧、舞台剧、戏曲、音乐剧、情景剧、快板、三句半、哑剧、双簧、诗朗诵、演讲稿、微电影、动画等各类剧本。联系电话:13979226936 QQ:652117037 公众号:剧本原创
